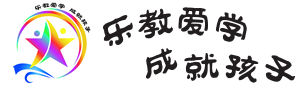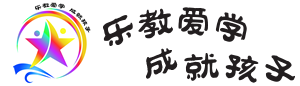这场音乐剧最让人醉心的,不是苦情鸳鸯凄美浪漫的情节,亦非有志青年、受压迫农民火拼土豪流氓的殴斗戏码,而是故事后半段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批判。
谈起经典爱情悲剧,西方世界有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,中文世界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, 多次被改编、翻拍,在不同的时代感动不同的世代。而《乌达与达拉》(Uda Dan Dara)是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家乌斯曼·阿旺(Usman Awang,1929—2001) 在1956年发表的作品,从诗歌进化成小说,接着于1972年登上电视荧幕,此后多次被改编翻拍,以电视剧或音乐剧上演。
2019年10月,舞台剧导演Dinsman(原名为Shamsudin Osman)将40捆稻秸秆运撒在吉隆坡的Padang Merbok,为《乌达与达拉》音乐剧搭建舞台。当时适逢雨季,闪电偶尔客串灯光,套上雨衣的观众犹如身在稻田,微风细雨中传来阵阵稻香,乃非一般剧场体验。
故事前半段讲述的是阶级地位如何分隔稻田中成长相爱的男女主角,乌达对着达拉说:“你来自上层的家庭,我来自底层的家庭。这个距离分开了我们。阶级的距离!”达拉母亲因担忧女儿未来日子受苦,属意将女儿许配给财大气粗地主家族;乌达知悉,横下心离乡背井到城里挣钱,以行动反驳“不自量力”的冷嘲热讽。
音乐剧带出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批判
这场音乐剧最让人醉心的,不是苦情鸳鸯凄美浪漫的情节,亦非有志青年、受压迫农民火拼土豪流氓的殴斗戏码,而是故事后半段对社会深层结构的批判。剧中一个名叫“Utih”的高人角色,总在关键时刻以本身智慧提点村民。例如,Utih认为若乌达积累财富,以满足达拉母亲的要求,届时让他俩成婚的不是彼此,而是金钱。金钱不仅让爱情变质,也让乌达与农民脱节。
Utih与地主对峙时,更点出“不曾种稻的人……却积累盗窃的财富,从插秧耕耘者的手中、从埋头苦干的硬骨头中”;然后坚持自己“拒绝崇拜金钱、拒绝为金钱所奴役,因为一旦成为名利的奴隶,就会制造罪恶与残暴。”
剧中更巧妙地安插了“Lebai”的角色,用华社的语境是“包头佬”,实为宗教师,在农民讨论是否起义时,频频感叹“这是上苍的安排”,村民只能忍耐、认命,并对所发生的一切心怀感恩。
然而,儿子在那场与地主流氓殴斗中阵亡的母亲有触动人心的控诉:“不,对杀害我儿子的人,绝无宽恕。我不要对上苍感恩,我的儿子没有犯错。乌达是我的依靠。他活着的时候,因为贫穷而受尽屈辱,几寸残稻、破烂棚屋。他进城时,稻米却被盗窃。乌达带着钱回来时,他被杀了。这是什么命运?感恩什么?”
强烈批判资本制度,控诉不公平的财富分配
一个叫Malim的角色说:“自古祖先总教我们接受与效忠。我们不曾质疑套在我们身上的制度与法令。这制度与法令公平吗?曾几何时,我们质疑过,为什么几个人,几个有钱的家族,可以坐拥几千英亩的土地与园丘?为什么我们几千个的农民,没有足够的土地,甚至连一虎口的土地都没有?为什么有钱人的家族,不曾亲手劳动耕地,却每个月坐享其成?为什么数千农民如我们,朝耕暮耘,只换来碎米残渣,偶尔以野菜配粥?为什么是他们来决定土地分配的规则?为什么盗窃土地的规则针对我们?为什么不反过来制定规则,让我们抢用豪门家族的土地,如果他们拒绝亲手耕耘?为什么不制定规则,让劳动者拥有土地?”
十万个为什么,最终激起村民起义的决心。“今天没有歌唱/除了铁钢与勇者的声音”;“是时候选择/以奴隶唱歌,抑或/以战士淌血?”
显然,此剧强烈批判资本制度,控诉不公平的财富分配。马来社会对“共产主义”极为排斥,但此剧左派色彩强烈,从劳动阶级角度出发,质疑土地拥有权的分配。有趣的是,即便在逾半世纪后翻演,依然意有所指,例如宗教人士“听天由命”的循循善诱,对照当下政治情境,不禁让人会心一笑。
马来政治里,其实不仅仅是种族与宗教论述,尤其在独立前后,左派的政治思想,也影响了知识分子,如文学家、文化人、新闻从业员等人。这场音乐剧对白优美、语颇隽永,甚称经典。它越过了爱情,摊开了刻意或不经意卷起的马来社会思想光谱。